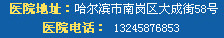戴冽,李谦华(中医院风湿免疫科)
痛风(gout)是由于嘌呤代谢紊乱和(或)尿酸排泄减少导致持续高尿酸血症(hyperuricemia)、形成单钠尿酸盐(MSU)晶体并沉积于体内引起的晶体性关节病。我国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为13.3%,痛风的患病率为1.1%,上升趋势明显。由于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患者也可以通过双能CT或者超声在关节中发现MSU晶体,年痛风、高尿酸血症和晶体相关性疾病协作网对痛风相关的概念和术语进行了规范,提出痛风的疾病状态包括临床前阶段和临床阶段。临床前阶段包括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无症状的MSU晶体沉积和无症状高尿酸血症伴MSU晶体沉积。临床阶段包括痛风、痛风石性痛风和侵蚀性痛风。痛风临床阶段的各种疾病状态可以同时出现。全球痛风发病率高,并且有上升趋势,因此各国对痛风患者的管理都非常重视。近5年发布的痛风相关指南就包括年中国痛风诊疗指南、年欧洲抗风湿病联盟(EULAR)痛风管理建议、年中国高尿酸血症相关疾病诊疗多学科专家共识、年英国风湿病学会(BSR)痛风管理指南、年中国高尿酸血症与痛风诊疗指南、年痛风及高尿酸血症基层诊疗指南和年美国风湿病学会(ACR)痛风管理指南等。这些指南对痛风患者的管理均强调了降尿酸药物治疗的重要性,但对降尿酸药物治疗相关的具体问题各指南推荐不一,有些还造成了临床的困惑。本文对此作了对比分析,希望有助于临床医师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指南推荐意见的内涵。降尿酸药物治疗的目标年EULAR首次提出痛风的降尿酸目标治疗,即血尿酸(sUA)达标并且要长期维持在目标值以下,以期溶解痛风石,清除关节内沉积的MSU晶体,防止新的晶体沉积,痛风可不再发作。此后的国内外指南均强调降尿酸目标治疗,并且大多数指南将具体的目标值定为sUAμmol/L,而对于伴痛风石、慢性关节病或痛风频繁发作的患者则应μmol/L。年BSR痛风管理指南更严格,将所有痛风患者降尿酸治疗的目标值定为sUAμmol/L。年ACR指南则认为,由于缺乏证据,不设定更低的sUA目标值来强化降尿酸药物治疗。这两种目标值哪种更优,尚待进一步的临床研究比较其疗效、安全性及费用-效益比。目前已知,sUA越低,已沉积的MSU晶体溶解越快,聚乙二醇重组尿酸酶培戈洛酶可以将sUA降至接近于0,从而迅速溶解痛风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sUA降得越低越好。我国台湾一项纳入例非痛风患者(~年)的研究显示,至年12月31日sUA处于极端低水平和高水平的个体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较高,而处于~μmol/L者死亡率最低。人体参考范围内的尿酸有重要的生理功能,尤其是抗氧化和神经保护作用,sUA过低可能会增加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因此多个指南提出了降尿酸治疗时sUA不应低于μmol/L。降尿酸药物治疗的指征对于痛风发作频繁、慢性痛风性关节炎或有痛风石的痛风患者,各指南均认为应予降尿酸药物治疗。然而,对于没有慢性损伤的早期痛风患者,如痛风第一次发作或每年发作仅1次的痛风患者,各指南的推荐不一。年中国痛风诊疗指南认为此时无降尿酸药物治疗指征,而年EULAR指南建议所有痛风患者均可以考虑降尿酸药物治疗;~年期间的中国指南、年BSR指南和年ACR指南均建议痛风第1次发作的患者需同时存在一种附加条件才予降尿酸药物治疗。年ACR指南还建议发作频次<2次/年的非频繁发作的痛风患者也予降尿酸药物治疗。然而,各指南对于附加条件的规定有所不同。总体而言,国外指南较严格,如年BSR指南规定为肾功能损伤、尿路结石病史、合并使用利尿剂及年轻时发作的痛风;年ACR指南仅限于sUAμmol/L、CKD3期以上和存在泌尿系结石。而~年期间3个中国指南或共识提到的临床情形则较多,除上述情形外,还包括sUAμmol/L、关节腔MSU沉积证据、高血压、糖耐量异常或糖尿病、血脂紊乱、肥胖、冠心病、卒中及心功能不全,认为痛风不仅仅会造成关节炎症,还可以对心血管系统、肾脏产生不利影响,缩短预期寿命,因此应该早期干预。对于无症状高尿酸血症者,我国的指南较为积极,推荐对于sUAμmol/L者启动降尿酸药物治疗,而年ACR指南则有条件反对无症状高尿酸血症患者开始降尿酸药物治疗。开始降尿酸药物治疗的时机对于有降尿酸药物治疗指征的痛风患者,痛风急性发作期能否开始使用降尿酸药物仍有争议。BSR痛风管理指南和我国的多个指南沿用传统观念,推荐在痛风急性发作缓解后再开始降尿酸药物治疗,ACR痛风管理指南年和年版均推荐在急性期即开始降尿酸药物治疗。痛风急性发作期不进行降尿酸药物治疗的理由是,sUA的剧烈波动可能会诱发或加剧痛风发作。随机对照研究发现非布司他mg组痛风急性发作的比例显著高于非布司他80mg组和别嘌醇mg组。ACR痛风指南的理由是小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显示,痛风急性发作的患者在吲哚美辛和秋水仙碱治疗情况下,别嘌醇mg/d组和安慰剂组疼痛缓解和30d内痛风发作次数无差异,但是别嘌醇组sUA显著低于安慰剂组。我们认为,降尿酸药物治疗是一长期过程,对于大多数无慢性病变的痛风患者而言,推后2~4周开始降尿酸药物治疗对其长期的疗效及预后影响不大。急性发作期痛风患者最主要的诉求是尽快控制急性发作,待控制后再与患者详细讨论降尿酸药物治疗,患者更易接受。临床真正的治疗难点是有严重慢性病变的痛风患者,这些患者可能几乎没有无关节肿痛的间歇期。此时可以考虑在有效抗炎治疗的同时加用小剂量的降尿酸药物。降低降尿酸药物的起始剂量可以减少诱发痛风急性发作。一项日本的随机对照研究报道,非布司他从10mg/d起始治疗的痛风患者即使不加用秋水仙碱,其急性发作的频率也不高于非布司他40mg/d并服用秋水仙碱0.5mg/d的患者。降尿酸药物的选择目前全球已上市的降尿酸药物包括抑制尿酸生成的药物(别嘌醇、非布司他和托匹司他)、促进尿酸排泄药物(丙磺舒、苯溴马隆和雷西纳德)和尿酸酶制剂培戈洛酶。在我国上市的药物仅有别嘌醇、非布司他和苯溴马隆,这3种药物均是我国各指南推荐的一线降尿酸药物,而EULAR、BSR和ACR指南均仅推荐别嘌醇作为一线降尿酸药物,其中不良反应在不同国家人群中的差异是导致我国指南与国外指南差异的主要原因。别嘌醇可发生致死性的别嘌醇超敏反应综合征(AHS),人类白细胞抗原(HLA)-B*阳性是发生AHS的高危因素。汉族人群携带该基因的比例为7.4%,而白种人仅0.7%。从药物经济学考虑,检测HLA-B*优于不进行检测。因此我国的痛风患者在使用别嘌醇前可行HLA-B*检测,阳性则选择其他降尿酸药物,以避免AHS风险。然而,现实情况是目前我国各地和各级医疗机构水平差异较大,该基因检测尚不能全面普及。非布司他在年ACR痛风指南作为与别嘌醇并列的一线降尿酸药物。但近期发现非布司他可能会增加心血管不良事件。多中心随机对照的合并心血管疾病的痛风患者使用非布司他和别嘌醇心血管安全性(CAREs)研究共纳入例合并心血管疾病的痛风患者,结果发现非布司他组心血管相关死亡风险及全因死亡风险均较别嘌醇组增加。由于白种人发生AHS的风险不高,因此EULAR、BSR和ACR指南均推荐别嘌醇作为一线药物,而非布司他则作为替代药物。汉族人发生AHS的风险高,尽管目前尚缺乏非布司他在我国人群的心血管不良事件数据,我国指南仍推荐非布司他也作为一线降尿酸药物。苯溴马隆在20世纪70年代上市后逐渐有与之相关的严重肝毒性报告,陆续在一些国家下市,目前苯溴马隆在德国、日本、新加坡和我国等国家使用。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年12月发布《警惕苯溴马隆的肝损害风险通告》,在年1月1日至年12月31日,收到苯溴马隆肝胆系统的严重药品不良反应报告23例。我国台湾地区年发布了苯溴马隆引起肝损害的药物不良反应警示,并引起苯溴马隆的处方量下降。但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苯溴马隆的风险效益评估后,认为苯溴马隆在我国治疗痛风获益仍大于风险,建议从低剂量开始,定期进行肝功能检查,避免同其他具有肝毒性的药物合用。因此我国指南仍然将苯溴马隆作为降尿酸治疗的一线药物。降尿酸药物的疗程国内外指南均明确强调,痛风患者的降尿酸治疗目标是必须长期维持sUA在目标值以下。近年研究表明,sUA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基因多态性,而不是饮食。因此,尽管循证医学的证据等级不高,近年的指南趋向于明确推荐降尿酸药物需要长期服用,以期维持sUA达标。然而,很多痛风患者不愿接受终身服用降尿酸药物。实际上,痛风患者是否需要靠长期服用降尿酸药物维持sUA在目标值以下,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该患者的综合降尿酸措施。降尿酸措施除经典的降尿酸药物外,还包括非药物治疗,如饮食控制、减轻体重、停用影响尿酸水平的药物如利尿剂等。伴合并症的痛风患者还可以有倾向性地选择同时有降尿酸作用的药物,如氯沙坦、阿托伐他汀、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年ACR指南考虑到非诺贝特的不良反应,不推荐痛风患者为了降尿酸而加用或改用该药。在已沉积的MSU晶体完全溶解后,如能通过以上措施使sUA长期达标,则有可能不必长期服用降尿酸药物。Perez-Ruiz等报道痛风患者降尿酸药物治疗5年后停用,13%的患者sUA可维持在~μmol/L且无痛风发作,服用氯沙坦、非诺贝特、停用利尿剂与sUAμmol/L有关。总之,近年国内外指南均强调长期服用降尿酸药物治疗的重要性,继续强调痛风患者降尿酸目标治疗及长期维持sUA达标的重要性。在无慢性病变的痛风患者中,不同的指南对降尿酸药物的指征有不同的推荐,总体而言,国内的指南指征较宽泛。痛风发作急性期能否予降尿酸药物仍然有不同的观点。基于我国患者特点,我国指南推荐别嘌醇、非布司他和苯溴马隆作为一线降尿酸药物,医师应熟知这些药物的不良反应和禁忌证。学习不同国家、不同组织制定的指南,更重要的是要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qjpu.com/zcmbjc/103388.html